作者:洛夫克拉夫特
1896年11月的下午,“我”已经在米斯卡塔尼克山谷里旅行了很长一段时间,沿途拜访了当地的居民,搜集某些宗谱学方面的数据。行程路线十分偏远曲折,而且充满了不确定的因素,为了抄近路尽快到达阿卡姆,我踏上了一条明显已经废弃了的公路。暴风雨来临时,恰巧走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自然没有找到更加好的地方避雨,只能看到了一间不怎么令人舒服的木头房子。房子坐落在一座岩石山的山脚下,两旁各有一颗不长叶子的榆树,窗户脏兮兮的,模糊不清,看不到里面,“我”却感到有什么东西向我眨眼睛。在我近期对宗谱学的研究过程种,我收集到了一些一个世纪之前的传说故事,故事让我对这样的地方产生了一些偏见。迫于恶劣的天气状况,“我”克服了内心的焦虑,毫不犹豫地推着自行车走到了房子的跟前。眼前的房门紧闭,看起来是那么神秘又引人遐想。
 (资料图片)
(资料图片)
“我”原本认为这个房子已经被人废弃了,但是通往房子的小路已经几乎被杂草覆盖了,依然保存完好,并不像是完全被遗忘了。“我”敲了敲门,内心中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恐惧。敲完门后,“我”就站在门口那块粗糙的、长满了苔藓的石头台阶上等。“我”转头看向了旁边的窗户和上面的玻璃,在风雨中发出卡塔卡塔的声响,也几乎被尘埃完全覆盖了,丝毫没有被破坏,完好无损。在“我”看来至少有人居住在这座房子。得不到任何应答,“我”又连续敲了几次门,还是没有人过来开门。试着去转动了一下那生锈的门闩,没有锁上,于是“我”推开门走进去。里面是一个狭小的前厅,墙上的石膏都脱落了,从房子里面传出了一个微弱的极其难闻的气味。把自行车也推进来,然后关上了身后的房门。前面有一道狭窄的楼梯,楼梯两侧各有一个小门,可能是通向地下室的。楼梯的左边和右边有几个通往一楼其他房间的房门,但是全部都关着。
“我”把自行车靠在墙边,打开了左侧的一扇门,走进去看到了房间很小,有一个低矮的天花板,微弱的光线从两扇灰蒙蒙的窗户里透进来,微微地照亮了房间。整个房间几乎没有装修,家具极为简单原始。房间看上去像是个客厅,里面摆放了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一座古老的钟表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壁炉架上面有一个巨大的壁炉。房子里放了一部分书籍和报纸,但是光线太昏暗了,“我”无法看清楚它们的封面内容,不过能看得出上面的复古气息。在这个地区,大部分“我”到访过的房子里都留存有大量过去留下的遗物,这间屋子里的东西却是彻彻底底古老的,这整个房间中,“我”甚至没有发现任何一样后革命时期的物品。可惜这里的家具都填过简单了,否则真的可以算的上事收藏家的天堂了。
“我”认真检查了这栋古旧奇怪的房子之后,那种一开始因为屋外的荒凉而心生的厌恶开始不断增强。究竟房间是什么东西让我感到恐惧和厌恶,很难说明;但房间内的整个氛围里似乎裹藏了一些异样的东西,让“我”想起了污秽的过去、引人不快的粗俗以及应该被遗忘的秘密。“我”甚至都不想在屋子里坐下,于是就一边徘徊一边研究起了刚才看到的那些书籍。“我”翻开了第一本让“我”感兴趣的书,那是一本中等大小的书,看起来非常古老,真没想到能在博物馆和图书馆之外的地方找到这种古书。书被保存的非常完好,最外层包裹着由皮革制成的封皮,还安装了金属扣件。这么精致的书竟然会被放在这样一座简陋的房子里,实在是令人惊讶。当“我”打开书的扉页后,它的罕见程度使“我”内心的惊讶于好奇变得更加强烈起来,这是一本由皮加费塔依据水手佩洛茨的笔记用拉丁文写的刚果游记,于1598年在法兰克福出版。对这本德·布里绘制的精妙插图的书早有耳闻,于是迫不及待地一页一页往下翻看,甚至忘却了刚才的不适感。书里描写的雕刻品真是由有趣极了,完全是根据想象和漫不经心的描述创作出来的,刻画都是黑人,却拥有雪白的皮肤和白种人的外貌特征。要不是一个极其细致的细节触动了“我”疲惫的神经,“我”或许还不会合上书,让不安的感觉又重新袭来。这本书总是会固执地想要对“我”展开它的第十二长全页插图,图上画的食人王国啊兹库斯的一家肉铺,整个画面都阴森森的,十分恐怖。这么一个微小的细节就能把“我”给搞心神不宁,真是让“我”感到丢脸。这一页插画的周边几页都是描绘啊兹库斯的美食的,还是不停地想起那副插画,恐惧和不安一直干扰着“我”。
“我”转而走向旁边的一个书架,去翻看了上面仅有的几本书籍。其中有一本是十八世纪时的《圣经》,还有一本差不多同一时期的《天路历程》,里面的插画是一些奇奇怪怪的木版画,是由年鉴编写者一塞亚·托马斯印制。还有一本科顿·马瑟写的《基督徒在美洲的光辉事迹》,十分破旧不堪。除此之外还有一下明显是同一时期的书籍。就在这时,“我”注意到一个明晰的声音,来自我头顶上的的房间发出的走路声。“我”简直惊呆了!刚才“我”不断地敲门,并没有人回应啊!很快“我”就反应过来,或许那个人之前一直在熟睡。这么一想,“我”就不那么震惊了,继续听着楼梯传来的吱吱喳喳的脚步声,那个人走下楼来了。他的脚步听起来十分沉重,里面也带着一丝谨慎和好奇。记得在进屋的时候,把房门关上了。脚步声听了一会儿,很显然那个人发现了“我”停在厅里的自行车。然后“我”就听到了那个人颤颤巍巍地摸索着门闩,把大门打开了。
门口站了一个外貌机器古怪的男人,“我”克制住了自己这一大声惊呼的想法。从整体看上去会给人一种衰老又贫困的感觉,身高超过了六英尺,身体结实又强壮,身材比例也很好。长长的胡须从脸颊上开始长,几乎将他的整个脸都给遮住了。甚至没有想到了,面色非常红润,皮肤也没有什么皱纹。高高的额头上散落了几缕花白的头发,双眼是蓝色的,有点充血,眼光里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激情和热情的情绪。“我”猜想了,他过去一定是一位高贵又帅气的额人。现在这副邋遢摸样,让“我”感到了非常无礼又带有攻击性。“我”没法说清楚他身上到底穿了些什么,给我的感觉就是一堆破布,堆在一双又高又沉的靴子上面。
“我”本能地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已经准备好好面对他的某种敌意。当他示意我做到一张椅子上,并用一种微弱的声音对说话的时候,还忍不住哆嗦一下。他的言语种充满了卑躬屈膝和假意迎合,带着很浓郁的北方口音,让我大为惊讶。直到他坐下去,跟我面对面地谈话,才仔细地辨认出他在说什么。
(原文)他向我传达了问候:“你是被困在暴风雨中了吧?幸亏你就在房子附近,进来躲雨就对的。我想我刚才是睡着了。要不然我一定会听到了你的敲门声。毕竟我已经不想以前那么年轻了,最近,除非是很强烈的声音,要不然我都听不到。你是不是旅行了很长的距离才走到这里?自从他们把阿卡姆的驿站,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遇到路人了。”
“我”回应打算去阿卡姆的,并且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不应该这么粗鲁冒犯地进入他的房子。
听完“我”的话,他便继续说道:(原文)“很高兴见到你,年轻人。在这里已经很难看到新的面孔出现了。最近的日子里,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能让我打起精神。我猜你是从波士顿过来的吧?我从来没有去过波士顿,但是我能一眼认出此城里来的人。1984年的时候,我们这来过一个男教师,但他后来突然离开了,之后再也没有见过他。”说到这里,老人突然轻声笑了起来,“我”问他笑什么?他没有回答。
有那么一会儿,他一直用一种过分亲切热情的态度跟我交谈。于是就问他是如何得到如此罕见的皮加费塔的《刚果王国》这本书。他犹豫了一下,不太像回答。“我”对那本书的好奇已经完全战胜了我初次看到这栋房子到现在积累的恐惧感。自我安慰道,提出了这个问题不会是一个令他尴尬到难以回答的问题。幸亏他还是慷慨地回答我。
(原文)“哦,你是说那本关于非洲的书吧?那是埃比尼泽·霍尔特船长在1968年的时候卖给我的。可惜他后来死在战场上了。”在之前的宗谱学调查中见过这个名字埃比尼泽·霍尔特,独立战争之后就再也没有找到于这个名字相关的任何记录。“我”对他说,能否对正在努力调查的工作给予帮助,并打算稍后向他询问相关的事情。
接着,他继续说道:(原文)“埃比尼泽在一艘塞伦商船上工作很多年,从每个港口都带回过不少猎奇的东西。我猜他是伦敦得到这本书的,他以前喜欢在商店里买东西。我曾经去过他家一次,就在一座山上,他在那而倒卖马匹。当我第一眼看到那本书的时候,我就被里面的插图吸引住了,所以就用一下东西跟他交换了这本书。这真是一本奇怪的书,让我戴上眼睛看看。”
老人在自己身上穿着的破布摸索了一下,找出了一副脏兮兮的眼镜,那眼镜简直太古老了,镜片是八边形的,镜框是铁的。戴上眼镜之后,他从桌子上拿起那本书翻阅起来并说道(原文)“埃比尼泽·霍尔特能读懂这本书里的一些东西。这是用拉丁文写的,我看不懂。我曾经找过两三个教师给我读了一部分,还有帕森·克拉克,不过大家都说他后来淹死在池塘里,你能读懂这本书的东西吗?”
“我”跟他说了能看懂拉丁语,并从整本书的开头部分找了一段翻译给他听。他看上去像个满足的孩子,即使“我”翻译又错误,也不能纠正“我”,听着“我”翻译。他坐的离“我”很近,让“我”着实感到不舒服,但是又不能冒犯他,所以一直不敢离开。不禁想到,他家里放着的其他用英文写成的书籍,他能看懂多少呢?
(原文)他说:“这些图能让人产生出许多奇怪的想法。比如前面这张图吧。你见过长成这样的树吗?上面长的大叶子从头一直垂到了地上。还有这些人,我感觉他们不是不是黑人,我猜他们是印第安人,或许是从非洲来的。你看这里,这儿画的动物们看上去很像个猴子,或者,是从非洲来的。你看这里,这儿画的动物看上去很像猴子,或者,是半人半猴的动物。我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动物。”边说边指着插画家在书上画的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
“不过,现在我要给你看一张我最喜欢的插画了。就在这儿,靠近这本书中间的位置。”老人的声音开始变得有点深沉,眼睛也变得更加明亮了。他的双手颤颤巍巍地在书上摸索着。随即,那本书被打开了,顺畅的几乎像是自动翻开的一样,这似乎暗示着有人经常翻阅这一部分内容。“我”所讨厌了的第十二长整版插图:一家开设在食人王国阿兹库斯里的肉铺。“我”尽量克制自己不断涌出的恐惧。插画的内容就不用多说了,相当的恶心。
(原文)“你觉得这幅画怎么样?你在这一带没见过这样的景象的吧我第一次看到这里的时候,就告诉埃比尼泽·霍尔特,‘这幅插画就像是某种刺激着你的神经、并且让你热血沸腾的东西!’我读过描写屠杀的话剧,类似屠杀缅甸人的话剧,我想象过那样的事情,但是没有看到过图画,现在这副插画里就有。我觉得屠杀的罪恶的,但是,我们不是生来就带着原罪的吗?而且,我们也都活着在罪恶之中。我每次看到这副插画,看到屠夫分尸,就觉得心里痒痒的。我就会一直仔细地盯着看看。你看到那个屠夫把一个人的剁了下来吗?那边的长凳还有他剁下来的一颗头颅,头旁边放着一只胳膊,地上的砧板还有另外一只胳膊。”
老人沉浸在自己令人震惊的狂喜之中,不停地喃喃自语,戴着眼镜满是胡须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描述的神情。之前隐约感受到的恐惧现在又重新强烈地涌上心头,真是厌恶年老又可恶的家伙。可是现在他又偏偏的那么亲密地靠近我。现在几乎是在喃喃自语了,那错索的声音比尖叫还是可怕。一边听着,一边不由自主地浑身颤抖。
(原文)“正如我所说的,这些插画引发人的思考。你知道,年轻的先生,我正坐在这儿看这幅插画。在我从埃比尼泽·霍尔特哪里拿到这本书后,就经常拿来看,尤其是在我听说帕森·克拉克在星期天戴着自己的大假发出门的时候。我曾经尝试过一些有趣的事情,就在这儿,年轻的先生,不要误会,我只是在把绵羊杀掉送去市场前看了看这幅画。那之后,我就觉得杀羊的过程变得更加有趣了。”老人说话的声音非常低沉,模糊到几乎无法听清他在说什么。暴风雨的声音,脏兮兮的格子窗户被吹打的格格作响,愈发逼近的暴风雨发出隆隆的声音,突然,一阵可怕的闪电击倒了这栋房子,整个房子都发生了震动,老子还是一直自顾自地呢喃低语,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切。
老人继续说道:(原文)“杀掉羊很有趣,然而你知道吗?那无法让我感到满足。欲望会给人带来奇怪的感觉。我们都爱着万能的上帝,但是年轻人,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向上帝发誓,看到这幅插画就会让我感到饥渴,想要拥有那些我养不起或者买不到的东西。你看,你现在就坐在这儿,是什么让你感到烦恼?我什么都没有做,只是在想象,如果我做了什么,会变成什么样?人们都说了肉会制造出血液和肉体,从而给予你新的生命,因此我就想,如果一个人能不断得到更多跟自己一样的东西,是不是就能活得越来越久?”到这里,他停了下来。
那本书就在“我”与他之间平整地摊开,第十二页的插画明晃晃地朝向我们。听到一滴液体滴溅得声音,随后看到了泛黄的书本上溅了什么东西。一开始以为是一滴雨,但是马上意识到了,雨水不可能是红色的。老人看到了书上的红色液体之后,马上向楼上的天花板望去,我也随着他的视线望过去,看到了那古老的天花板上的石膏层已经松动了,印出了一摊形状不规则的深红色液体的印迹,而且范围还在不停地扩大。“我”没有尖叫,也没有逃跑,只是闭上了眼睛。过了一会儿,巨大的雷电劈了下来,将这间被诅咒的房子连同它里面的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炸的粉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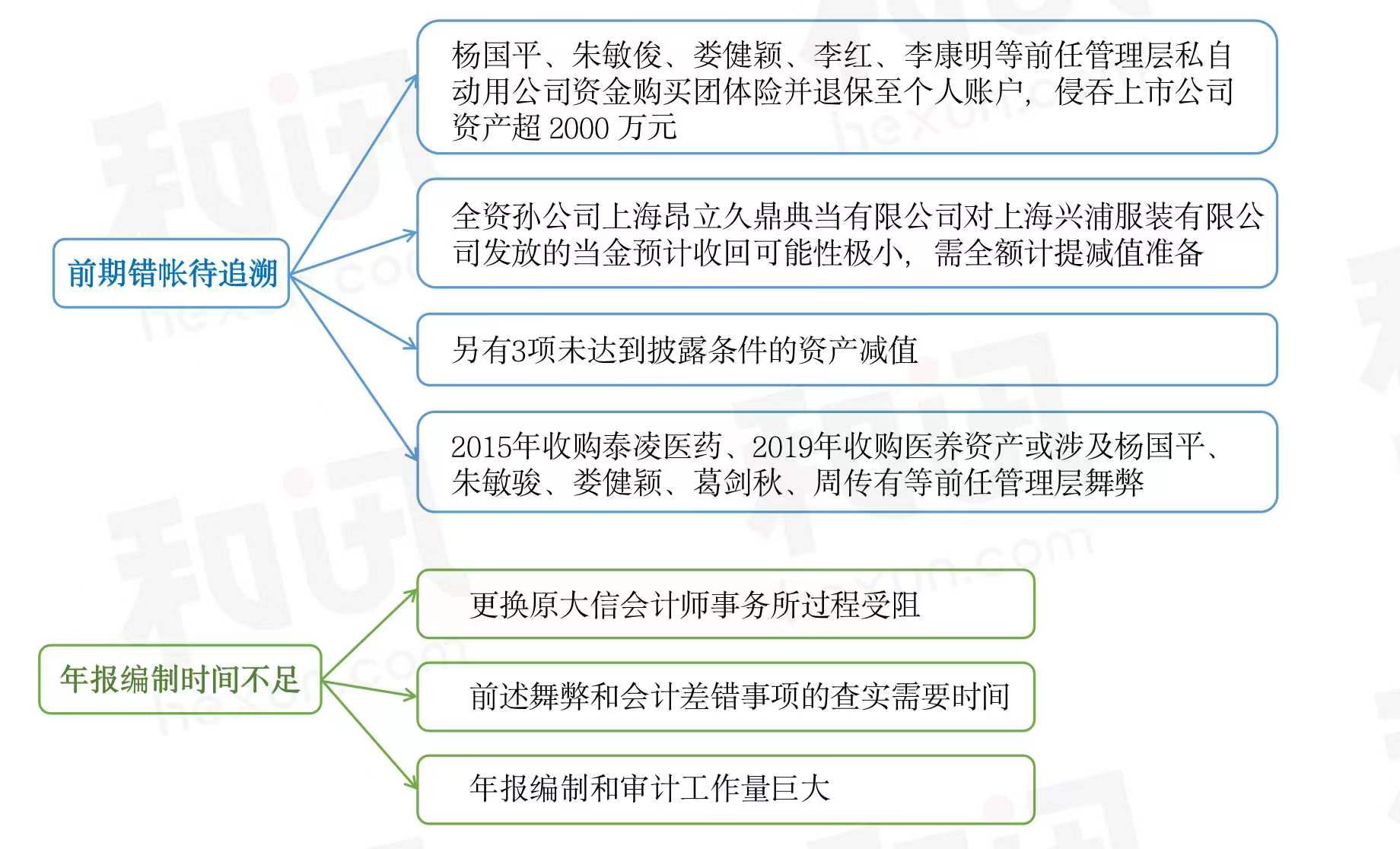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
营业执照公示信息